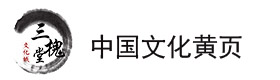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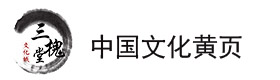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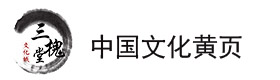
来源: 发布时间:2017-11-24
莫言,原名管谟业,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。获奖理由: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。据不完全统计,莫言的作品至少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。
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
大江:距《红高粱》时隔十二年之后,你又拍了《幸福时光》,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,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?
后来看到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,那是在《收获》上,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,一看是莫言写的,我就把它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。到了晚上,一口气读完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,也能代表时代的变化,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。
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表现不好。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,到了新的时代,他的观念,生活甚至生存,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,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。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,不能是劳动模范,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。
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,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。但最后我是觉得《幸福时光》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。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,没有像《红高粱》那样得到他太多的“真传”。
而且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,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。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,就是这个题材本身就富有挑战性,而张艺谋非要拍,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。绕来绕去,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。这与《红高粱》的直接“吼”出来不同。
当然我看了以后,有的地方我还可以会意,但观众看了以后就会忘了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。
越来越少的读者与观众
大江: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,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,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?
张艺谋: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。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,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,特别愿意思考,中国的十年“文革”结束后,日本的二战结束后,包括欧洲,美国,在之后的一段时期,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,每个人都很开心,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。现在是和平时期,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行。和平时代丰衣足食,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,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,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。
张艺谋: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。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。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放一张白纸,或摆台电脑在面前,让我从零开始。所以,我很佩服作家,他怎么就能写出这么多故事来呢?
作家自由与导演无奈
大江: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。我还有一个问题,生活在目前的中国,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?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,我不想问,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,我没法回答,我只是说: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,你抽象地让我回答,我回答不出来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,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,我们的录像带很长,你们可以随便说说。
张艺谋:那我就浪费一段吧。其实我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,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,最关心的是人,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。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的去问过自己,你到底想弄什么?我有点像逛商店,不知道想买什么时,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,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。
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,对我来说就是颜色,对!颜色。我对视觉的东西很敏感,很迷恋的,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,我就会觉得很兴奋。
莫言: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,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,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。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,放下后永远捡不起来了,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最后都做了中篇处理。
当时觉得很兴奋,写了三五万字,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。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出现。从某种意义上,我是跟着感觉走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不管你做什么,不管你写什么,都要成为原创性的,唯一的。别人做过的,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。最好是别人没写过,用的也是自己没有用过的手法。
但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不过再困难也要有自己追求的目标,哪怕实现了百分之三十,这部作品就非常好。
张艺谋:这点也太自由了,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,不写了。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,剧本弄好了,班子搭好了,突然找不到感觉了,就觉得真没劲,但又非干不可,还得挺着,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,充满信心,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。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,因为你没有激情。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,完全身不由己。
莫言: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。
张艺谋:你多方便。
大江:我还是没有莫言这种情况,我一旦写起来就会把这部作品写完,我的习惯是重复,不满意的地方改,往短里改,一般改六次,就达到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。我这样说,张导演可能有些失望。因为他刚说小说家可以随便扔。
张艺谋:碰上一个不扔的作家。(众笑)
正如世界著名币章大师罗永辉先生设计的那样,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蹴而就,需要一步一步的累积直至文学的巅峰。
|

| 地址:无锡市梁溪区吉祥大厦6楼 | 电话:0510-85112050 |
| Copyright©无锡三槐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| 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编号:苏B2-20201445 苏ICP备16062224号-1 |